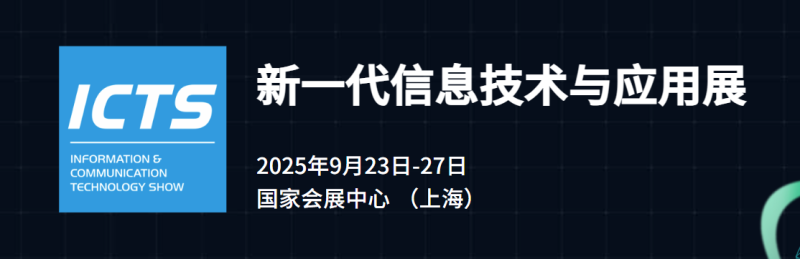《传习录》九五:段誉的“六脉神剑”
侃问:“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先生曰:“初学功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无时,莫知其向’,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功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于功夫上又发病。”
薛侃问:“秉持志向的时候,稍有偏离就会心痛,一心只顾念着这个心痛,哪还有时间去说其他闲话、管其他闲事呢?”
先生说:“初学时下这样的功夫也很好,但是自己要明白心中的神明原本就是如此——‘吾心即是宇宙,本无所谓出入;宇宙即是吾心,它自有它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让所下的功夫有着落。如果只是死死坚守自见的志向,恐怕会在执着于功夫上出差错。”
金庸笔下有个人物叫段誉,段誉怀揣一项绝技——六脉神剑。然而,他并不知道如何得心应手地驾驭这一绝技。常常是想要发挥时施展不出来,等到眼见得要绝望了,忽然又见了神奇。
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总结,段誉的这项绝技,似乎只有在与让他动心的王语嫣姑娘有关时,才能正常发挥。
段誉的六脉神剑,与动心有关时才能发挥。王阳明讲的“心即理”,反倒是在无心时效果才更好。
薛侃是王阳明的学生,字尚谦,号中离,广东揭阳人,中过进士,是王门闽粤一带弟子中的佼佼者。他提出“持志如心痛”之说,不得不说,是个做学问的奇才。孟子笔下的舜“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孔子眼中的颜回“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都是对善言正行格外敏感的人。薛侃“持志如心痛”——因为心里有志向,只要一偏离就会心痛,以“痛”的方式来提醒自己专注己志。这样的学者,天生就是一个圣贤胚子。
王阳明首先肯定了薛侃的“初学工夫”。
孔子讲:“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包括《论语》在内的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典籍中,并没有这句话。这句话出自《孟子·告子下》,是孟子的弟子记录下来的——孟子在同弟子们讲到牛山生态环境被破坏导致牛山外显的“性质”发生变化时,引用孔子的话来说明“良心”得其养与不得其养的差别。
王阳明在这里,借用孔子的这句话来说明“良心”“天理”的存养道理。“操则存,舍则亡”——对于常人而言,当他拥抱良知时,则天理存养在心;当他丢弃良知时,则天理从其心里消失。因为常人有时会贪恋私欲,失去良知,失去天理。
与此同时,天理良知又是“出入无时,莫知其乡”的,他本来就永恒地存在于我们的心之本体中,人完全不必去时刻提醒自己要不要“操”,会不会“舍”,过分的“有心”“着意”反而会像没有完全驾驭六脉神剑的段誉一样手忙脚乱,迷失方向。吾心即是宇宙,本无所谓出入;宇宙即是吾心,它自有它的方向。一个人倘若能真正复原自己的心之本体,达到这样的境界,实际上也就出神入化,像后来成功驾驭六脉神剑的段誉一般,信手拈来、游刃有余了。
每个人的心中,原本就存在一面“随感而应,无物不照”的镜子,只是因为不肯下“去人欲,存天理”的功夫,各种欲念、尘埃逐渐蒙蔽得它失去了本来面目,慢慢地变得不那么光亮了,久而久之,人连心中这面镜子的存在也忘记了,却一味地试图以自己有限的生命和失去本心的混沌与梦寐洞悉整个宇宙,全然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节奏。
王阳明的“学为圣贤”,不是为自己求一个人生的归宿,而是以自己为例,为天下人求一个为学的出路。从个人的“学为圣贤”,到人人“学为圣贤”。必然要找一个可“皆备于我”的出路,这个“皆备于我”的只能是“心即理”——吾心即是天理,天理皆备吾心。
作如是观时,薛侃这样的弟子尚且讲“持志如心痛”——心怀志向时稍有偏离便会感到“心痛”。这哪里还是在讲那个人人“皆备于我”的心?分明是少数明心见性者的心。所谓不破不立,王阳明求的可是人人皆可“学为圣贤”。这个“心即理”哪里是思虑造成的天理存于吾心,而是人心本来就具足的。“去人欲,存天理”的功夫只是让本然具足的东西显现出来而已。
据说,有一次王阳明带诸弟子去登山。山高路远,不少弟子中途就放弃了。当然,也有不少弟子随老师一起登上了山顶。登上山顶的弟子都气喘吁吁,唯有王阳明气定神闲,在诸弟子狼狈不堪时反而来了兴致,要和诸弟子比赋诗。这种情况下,王阳明居然一口气赋了三首很有意境的诗。弟子们惊讶不已,追问老师为什么精力这么好。王阳明告诉登上山顶的弟子“山高万仞,我只登一步”。
这哪里还是薛侃“持志如心痛”的谨严、刻苦?内而观之,吾心即是吾身,吾身即是吾心。外而化之,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天理无不自在吾心。
真正练成六脉神剑的段誉最后完美实现了“人剑合一”,“心即理”“致良知”的王阳明何尝不是另一种境界的“人剑合一”?